《讀書》首發 | 馬嘯:發展的偶然性
2024/05/03 信息來源: 《讀書》雜誌
文字🚵🏻♀️🔃:馬嘯| 編輯👱🏼:燕元 | 責編:安寧編者按🚐:比較政治學者阿爾弗雷德·斯蒂潘曾說👱🏼♂️🧑🏿🎓,人們只有在深入地了解其他國家後才能真正了解自己的國家🍭。以蘭小歡在《置身事內:中國政府與經濟發展》一書對中國經濟發展特殊經驗的解釋為參照,馬嘯與其自身在埃塞俄比亞的調研進行了比較分析,意識到許多已經被廣為接受的關於一國經濟社會發展的理論背後往往暗藏著一些被忽視的初始條件,而這些條件的出現可能是相當偶然的👩🏿🎤。將中國置於比較視野之下能幫助我們更好地“錨定”中國發展歷程的一般性理論意義🔍,有助於對中國當下經濟轉型和其他發展中國家發展道路的理論探索。本文特轉載《讀書》首發文章,以饗讀者🏋🏼♂️🧑🏻🦰。
如果我們把人類歷史比作一天的話,國家這一特殊組織直到這一天最後的半小時才出現。在這一天的大部分時間裏,不同地方的人們都過著相似的貧窮生活✌🏼;國家的出現意味著人類文明迎來了驚鴻一躍🐥,但同時也帶來了巨大的財富鴻溝。這種財富差異既存在於個體間,也非常顯著地存在於不同國家之間。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統計,二〇二二年世界上最富裕國家的人均國內生產總值是最貧窮國家的五百余倍。為何人類社會在短時間內會出現如此巨大的發展程度差異?國家在其中又扮演了何種角色?這一問題堪稱社會科學研究皇冠上的明珠👦🏻。在過去的幾個世紀裏,那些對人類產生了深遠影響的偉大思想家,從十八世紀的斯密🧝🏻、李嘉圖🕙,到十九世紀的馬克思、韋伯,再到二十世紀的熊彼特🥯、波蘭尼👷🏻、哈耶克等,都嘗試回答這一問題。

亞當·斯密《國富論》(1776年版)首頁
相比古典自由主義對市場這一“無形的手”的推崇🤐,“二戰”以後社會科學的一個重要共識是👐🏻:無法繞開國家這個組織談論發展⚒🙆🏼♂️。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經濟史學者亞歷山大·格申克龍在《經濟落後的歷史透視》一書中🦸🏼,提出了“後發優勢”的概念。他認為後發地區在工業化進程中的相對落後狀態反而是一種優勢:這些國家可以利用人類社會迄今為止所積累的技術知識實現“跳躍式發展”💓。而實現後發優勢的重要條件之一是國家在資源(例如資本)調動的過程中能夠發揮支配作用👉。
後發優勢理論在現實中很快得到了檢驗🙍。二十世紀六十至七十年代,日本😪、韓國等東亞經濟體在政府強有力的產業政策的引領之下實現了耀眼的增長💃。八十年代當“把國家視為問題”的新自由主義政策開始在西方老牌工業國大行其道之時👨🏼⚖️,這些新興經濟體快速工業化的經驗在西方學術界引發了“找回國家”的反思,催生了諸如“發展型國家”“嵌入性自主”等概念🌅。這一脈理論認為🤟,這些新興經濟體之所以能實現快速工業化,關鍵在於有一個強有力的、不受特殊利益影響或俘獲的“自主的”國家機器,其通過製定符合本國稟賦優勢的經濟政策引導市場發展,進而加速實現工業化。

Peter Evens, Dietrich Rueschemeyer, Theda Skocpol主編的《找回國家》(Bring the State Back In,1985)封面
在“發展型國家”學說出現和發展的同時,新製度主義關於發展的解釋同樣受到了關註。以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道格拉斯·諾思為代表的製度主義學派,從更長的歷史視角審視國家間發展差異的成因。他們提出,國家作為經濟活動的最終裁決者,其能否保護產權、執行市場契約,同時又不成為經濟的掠奪者,是影響國家長期繁榮的根本因素。然而上述兩個目標之間卻有著一定的張力,一個強大到能夠保障產權的國家必然能夠侵犯產權🟥。在新製度主義學派看來🛹,國家要達到這些目標,必須符合特定的製度特征,例如對於政府的限權和法治等,英國“光榮革命”之後形成的憲政民主體製是這種製度的代表👨🏼🚒。新製度主義與“發展型國家”理論存在著明顯差異,後者強調國家的“有為”(對經濟活動的積極幹預和調控)🤤🫃,而前者則強調國家“為所當為”(保護產權)和“止於不可不止”(掠奪經濟)。但相比於古典自由主義和新自由主義學說,這兩種理論都突出了國家這一組織作為市場的參與者或裁決者的重要作用🤸🏿♀️。
中國在過去幾十年的快速發展為這一研究議題提供了新的素材。中國經濟的持續快速增長不僅使得世界人口的近五分之一整體邁入了中等偏上收入社會的行列,也對全球減貧事業做出了重大貢獻👨🏽🔬🎒:按照世界銀行的標準🍿,中國在過去四十年裏減少的貧困人口占到同期全世界減貧人數的75%🫎🦵🏽。然而中國的現實與“發展型國家”或新製度主義解釋均存在著差異。雖然中國政府對經濟建設的深度參與很容易讓人將其與“發展型國家”聯系起來🏋🏿♂️,其特征與“發展型國家”的定義仍存在明顯出入☺️。例如“發展型國家”理論認為政府的經濟部門通過協同一致的政策引領市場的發展;而在中國經濟政策的製定與執行過程中🍇,無論是在政府的橫向(不同的政府職能部門間)還是縱向(不同層級的政府間)維度上,均存在著顯著的部門職能差異和張力,不存在諸如日本通產省這樣單一的👨👩👦👦、行為邏輯一致的經濟政策“領航機構”。而如果從製度主義視角審視👩👧👦,中國也與西方典型的“限權-分權”體製存在不同🤞🏿,執政黨和政府在經濟社會治理的各個維度都扮演了主導性的角色,不存在與其分享權力的製度主體。如果說“發展型國家”和新製度主義理論均存在局限,那我們又如何解釋中國經濟騰飛這樣一個具有重要現實意義的案例呢🤵🏼♀️?
蘭小歡在《置身事內:中國政府與經濟發展》一書中對這一問題進行了系統性的回答。全書分為上下兩篇,分別從微觀機製與宏觀現象兩個視角解釋中國發展的條件、過程和存在的問題。本書的一個核心觀點是,不應簡單地將發展過程與發展的結果等同。社會科學關於發展的理論往往基於對若幹成功國家的政策或製度特征的總結。這種“橫截面”式的結論往往忽視了發展本身是一個漫長且復雜的過程,可能需要經歷幾代人的時間。把對發展結果(發達國家)總結形成的經驗嫁接到尚未或正在經歷發展過程的後發國家🧏🏻♀️,無異於刻舟求劍➜。對於那些尚未建立起良好市場機製的發展中國家,政府在資源動員和配置,以及建立和完善市場經濟的過程中應該發揮重要的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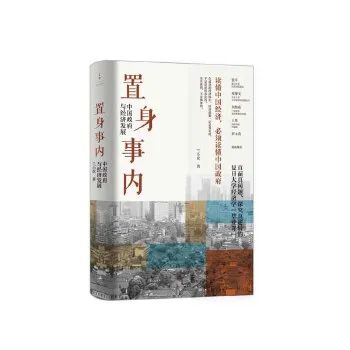
《置身事內:中國政府與經濟發展》,蘭小歡著🤾🏽,上海人民出版社二○二一年版(來源:dangdang.com)
具體到中國,在改革開放初期👩🏼🔧,政府掌握了社會中絕大部分的資源,因此如何調動政府部門的積極性,對提高整體經濟效率至關重要。對此,中國的做法是采用“屬地管理”和“地方競爭”相結合的方式,將經濟發展納入地方主政官員的升遷考核,使地方官員將經濟增長作為工作重點。一個地方經濟能否增長,很大程度上取決於該地企業能否在更大的全國乃至全球市場的競爭中獲勝👃🏼,以及諸如資本、人才等生產要素能否持續地流入該地。這就驅使地方政府既要按照市場規律來配置資源,同時又盡量克製掠奪市場等行為✂️💁🏻♀️。因此🦠,各地政府不僅競相出臺優厚的營商政策(例如廉價的土地、完善的基礎設施和稅收優惠及補貼)🏌️🙏🏽,一些地方政府甚至直接“下場”,通過財政出資成立產業引導基金等形式促進新興產業的發展。這種“官場+市場”的競爭使得政府和市場的邊界變得模糊,地方政府如同市場中的企業一般通過競爭參與到發展的過程中,成為推動經濟增長的強大動力。
當然,地方政府之間的競爭與企業間的市場競爭也存在著顯著不同。蘭小歡在書中提到,大部分政府官員並不需要為失敗的產業政策負責,而企業決策失誤則可能面臨被市場淘汰👩🏽🌾;相比市場競爭產生的“正和效應”🧑🏽🎨,地方政府圍繞生產要素之間的競爭更像是“零和博弈”,因此更容易導致地方保護主義和貿易壁壘;此外,相比企業間的長期競爭🫰🏽,地方政府受主政官員任期的影響更容易出現短視行為👨👩👧👧,導致債務等長期風險。某種意義上,中國發展過程中出現的一些問題(例如高房價、地方政府債務、產能過剩等)和取得的成就宛如一枚硬幣的兩面,“官場+市場”競爭的激勵結構讓中國在快速追趕發達國家的同時也付出了一定的代價。隨著中國改革發展進入深水區👶🏼,單純的模仿和學習先進國家技術的發展路徑上升空間已經很小。蘭小歡在結尾中提出♘,能否成功地從“組織學習模式”轉變為“探索創新模式”👨🏼✈️,取決於迄今為止總體較為成功的“生產型政府”能否逐步地向“服務型政府”轉變。
如果說基於理想發展目標(即發達國家)的特征抽象化而成的理論並不一定適用於廣大發展中國家的話,那麽中國的發展過程,對發展中國家又是否具有借鑒意義呢🥂?二〇二三年暑假,我和幾位同事及研究生前往埃塞俄比亞,走訪了該國的聯邦和地方政府機構、企業、科研院所等,嘗試理解該國發展的現狀和問題。作為非洲屈指可數的未被殖民的國家,埃塞俄比亞走出了一條較為獨立的發展道路。在很多維度上,埃塞俄比亞的發展路徑與中國存在相似之處。例如,埃塞俄比亞的憲法規定土地為國家所有,土地因此成為政府可以調配的重要資源🦁📢。作為一個聯邦製的國家🔠,埃塞俄比亞地方政府在經濟社會發展中具有較大的自由裁量權🫴🏽🗑,不同州之間圍繞投資等要素也存在競爭;此外,埃塞俄比亞政府也深度地參與到經濟發展的過程中,在聯邦政府層面設有計劃發展部、貿易與區域融合部🈵、工業部、創新與科技部♉️、投資委員會等經濟政策部門🤴🏻🛴。這些部門出臺了一系列產業政策鼓勵投資和吸引國內外投資🧜♂️🧎🏻。埃塞俄比亞政府早在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就製定了指導經濟發展的首個“五年計劃”,雖然連續性不及中國,但之後也陸續出臺多次👨👦🧤。在埃塞俄比亞各地還存在不同規格的經濟開發區👰♀️,有些由聯邦政府設立🖱,有些由地方政府設立👨🏼🚒,也有由外國企業(主要是中資企業)投資設立的開發區。這些經濟開發區不僅擁有相對良好的基礎設施(例如穩定的供電供水),還給予了入駐企業一系列稅收和雇傭方面的優待🤛。由於這些相似性⚇,埃塞俄比亞經常被人稱作“非洲小中國”。

埃塞俄比亞中部的阿瓦薩(Hawassa)工業園,由埃塞俄比亞聯邦政府投資建設。作者攝於2023年8月
然而埃塞俄比亞的發展似乎不如中國那樣一帆風順。二〇二〇年以來,受族群關系緊張的影響🚺,埃塞俄比亞政府與地方勢力斷斷續續地打了幾場內戰。戰爭的一個直接後果是外匯短缺(政府需要進口武器)♿️🐣,本幣比爾(Birr)大幅貶值,美元兌比爾的黑市匯率是官方匯率的兩倍👨👨👧👧。埃塞俄比亞工業基礎極為薄弱,在日常生活用品中,小到不銹鋼鍋、電扇等都需進口,而出口主要依靠咖啡等農產品👱🏿♀️。二〇二二年埃塞俄比亞貿易逆差達到了一百四十七億八千萬美元。政府為了獲取外匯,對進出口企業采取強製結匯的措施。出口企業用黑市匯率進口設備和原材料👮🏽♂️,產品出口賺取的外匯卻被政府以官方匯率結匯🧔🏿,出現了“生產越多,虧損越多”的怪象🪈。企業如果想將賺取的利潤轉成美元匯回本國,則需要獲得埃塞俄比亞央行的審批🐆,而等待過程常常遙遙無期。我們在調研中發現,除了首都亞的斯亞貝巴周邊的少數工業園區,政府斥巨資建設的各地工業園入駐率並不高,而為數不多的出口企業🍮,因為嚴格的外匯管製👰📱,大部分主動縮減了產能,一部分則幹脆轉向了進口替代業務。
此外👨🏼🚒,和絕大部分發展中國家一樣👩🏼🍳,埃塞俄比亞也受腐敗問題的困擾。二〇二二年透明國際(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公布的腐敗感知指數排名中,埃塞俄比亞位列第九十四名🏄🏼。在與一名在當地經營酒店的中國商人的交流中得知🪤,其酒店的推拿服務(主要面向當地的中國人)每次收費折合約三百元人民幣,相當於當地普通人一個月的收入,前來消費的本地人主要是政府官員👩🏽🔧,他們的正常工資顯然無法支撐這類消費🥷🏻🚅。雖然政府職位意味著獲得體面生活的機會,但其招錄過程卻比較隨意。埃塞俄比亞並不存在全國性的公務員招錄考試👨🏻🦼➡️,各級政府部門通過在報紙上刊載廣告自行招聘人員。可以想象,缺乏統一標準的招錄會為尋租創造空間。在個體腐敗行為之外也存在著較為普遍的製度性腐敗🍿。一名中方投資的工業園的管理人員告訴我們,每個進出工業園的集裝箱都要被當地政府收取一筆額外的“過路費”。埃塞俄比亞地方政府與聯邦政府之間的關系也比較微妙🤮,兩者經常處於競爭甚至對立的關系🐵,而這種關系在摻雜了族群政治的因素之後變得更加復雜🧖🏿♀️。
雖然經過了長期的發展努力👩🏿,埃塞俄比亞的人均GDP至今仍徘徊在一千美元上下💡,在聯合國認定的“最不發達國家”之列。該國今天面臨的很多問題,例如外匯短缺、匯率雙軌製、腐敗🦸🏻♂️、政策不協調等🙋🏼♂️,在中國改革發展的過程中也曾出現過🌬。但這些問題並未阻礙中國經濟的起飛,在後續發展過程中我們也逐漸克服(或部分解決)了上述問題。或許有人會說,埃塞俄比亞主要是受到內戰的困擾🦹🏽。然而跨國數據顯示🫸🏻,導致內戰的最顯著因素恰恰是貧困:人均收入每下降一千美元👱♂️🙆🏿♀️,內戰發生的概率增加41%🥮。當收入增加,發生沖突的機會成本上升👱♀️,內戰發生的概率就會下降。人們常說戰爭是政治的延續🤌,內戰的發生歸根結底還是可以溯源至前文所述的諸多問題交織構成的低發展水平的均衡。
仔細審視埃塞俄比亞的現狀和中國改革開放的初始條件,會發現兩者間還存在著一些細微但重要的不同🫶🏼。中國在改革開放之前已經經歷了三十年的工業化進程,形成了一套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並完成了初級產品的本國替代。根據蘭小歡的觀點,改革開放前各地積累的工業知識和體系(包括在這一過程中訓練的工人),為改革後地方鄉鎮企業和私營企業的發展奠定了基礎。這些企業最初的經營者,很多依靠的是國有工廠的技術基礎,另外一些則通過與國營工廠的“聯營”等形式進入生產製造環節📤。與之形成對比的是,埃塞俄比亞的工業基礎仍然極為薄弱📟,二〇二二年工業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僅為22.72%。該國通過農產品出口換取的寶貴外匯首先需要滿足日用必需品的進口,無法用於企業進口先進設備🚵🏿。當企業不掌握技術優勢時便很難具備全球市場的競爭力,於是陷入了“外匯短缺—工業升級困難—逆差持續”的怪圈。此外,工業基礎薄弱也意味著本地缺少熟練的技術工人,外企在埃塞俄比亞投資時更傾向於使用外國雇員操作關鍵技術,延緩了工業知識和生產技能向本地轉移的過程。

咖啡、牛油果等經濟作物的種植和出口仍是埃塞俄比亞重要的外匯來源🚼。圖為埃塞俄比亞中部錫達瑪(Sidama)地區的一個女性為主的農場🙇♀️。作者攝於2023年8月
我們在埃塞俄比亞觀察到的另一個現象是地區間發展水平和稟賦巨大的差異。首都亞的斯亞貝巴是包括非洲聯盟在內的多個國際組織總部所在地,有著非常完善的基礎設施,同時還是非洲最大航空公司埃塞俄比亞航空的主要中轉地🔗。但是一出首都就是另一番景象:連接城市間的道路不少仍然是土路,電力供應也並不是很穩定,中小城市還存在著治安問題👂🏽。這種區域間的巨大落差使得聯邦製的一個優勢,即次國家轄區間的競爭,無法得到充分發揮。雖然埃塞俄比亞政府在各地都投資建設了工業開發區,但因為交通👆🏻🤽🏻♀️、供電、工業基礎等條件的限製🤲,僅首都周邊的工業園區對外國投資者有一定的吸引力🤽🏻♀️💁🏿。蘭小歡在解釋中國發展過程時提及,只有當大多數地區的工業基礎相差不大時才能在工業化進程中孕育出地方競爭🐅,否則資源會迅速向優勢地區聚集💛。中國在改革開放初期擁有一個地理上相對分散的工業體系,為後續各地“各顯神通”的發展競爭奠定了基礎👦🏽。這種相對分散的初始工業分布,很大程度上要歸因於六十年代開始的“三線建設”🏊:因外部戰爭威脅而向內陸進行的轉移,使得廣大的中西部省份也擁有了基本的工業體系和基礎設施。此外💧,規模也是兩國間一個不容忽視的差異。埃塞俄比亞從人口和面積來看與中國的一個大省相當。在中國的一省之內同樣存在著中心(省會)城市和邊緣城市的差異,但因為中國有著數目眾多的省份,發展競爭仍然可以在不同省份間展開。改革開放初期,雖然沿海地區和內陸之間在招商引資的條件上存在巨大差異🧹,但因為中國海岸線漫長🫦😤,在沿海省份之間仍然出現了競爭。而在埃塞俄比亞則不存在與首都條件接近的地區,真正有意義的區域間競爭因此也難以產生。

埃塞俄比亞首都亞的斯亞貝巴的友誼廣場(中國援建)🌔。作者攝於2023年8月
仔細審視兩國間的這些差異🧏🏽♂️,可以發現中國在發展初期擁有的有利條件不是通過簡單模仿能獲得的特征。這些特征要麽是長期發展積累形成的路徑差異(例如發展初始階段的工業基礎)🖕🏿🐚,要麽是歷史“無心插柳”的意外(例如“三線建設”導致分散的工業體系),或者就是一些無法習得的客觀特征(例如國家規模等)。此外,兩國在其他維度上的差異🥴,例如中國官僚體系的相對專業和獨立性,以及主體人口的文化融合等💪🏼,也並不完全是近現代的產物🔃。
這些無法習得的差異讓我想到了學術界對製度主義理論的批評。製度主義學派強調完善的製度(例如民主🧔🏽♀️、法治等)對於發展的促進作用,卻忽視了形成這一系列製度的過程中可能會產生的代價⇨。這些代價既包括對既有社會關系的艱難調整—很多製度的變革可能需要通過代價高昂的戰爭或革命實現;也包括了製度形成後產生的新的成本。例如,在一個工業化尚未起步的國家▪️,過早建立嚴格的產權製度🛒,會大幅增加諸如土地等生產要素從低生產率行業(農業)向高生產率行業(工業)轉移的成本。正是因為忽視了製度形成的代價,才產生了蘭小歡所說的將發展結果(例如完善的製度)錯當成發展手段的問題。因此,在討論某些特征條件(無論是製度還是政策)對發展的影響時,我們首先應考慮的是這些特征是如何形成的,在這一過程中又付出了什麽樣的代價💅🏽。當另一個國家以發展為目標嘗試復製這些條件時🧗🏿♂️,可能未必能負擔創造這些條件的巨大成本。
以發展型國家為例,它們的突出特征之一是政府對社會資源有強大的調動能力。而一個強國家的產生🤦🏻♀️🌪,按照米格代爾的觀點🐳,需要戰爭👩🎤、大規模移民等能對既有社會結構形成破壞性沖擊作為必要條件🫣🪮,以及獨立的官僚體系、合適的國際環境等充分條件(Migdal, Joel S. Strong Societies and Weak States: State-Society Relations and State Capabilities in the Third World.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8)。例如🙆🏿♂️,斯萊特等人在探討東亞發展型國家的緣起時,指出這種特殊的國家-市場關系只有在持續的內外部安全威脅以及資源約束的共同作用之下才有可能出現(Doner, Richard F., Bryan K. Ritchie, and Dan Slater.“Systemic vulnerability and the origins of developmental states: Northeast and Southeast Asia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59.2 (2005): 327-361)而上述無論哪個條件,對於一個沒有恰好經歷過這些的國家來說🦹🏽♂️,它們的“再現”成本都是極其高昂的。因此,我們不僅不能簡單地將發展結果當作發展過程,在評價某一特定發展過程時,也需要思考其產生的特殊初始條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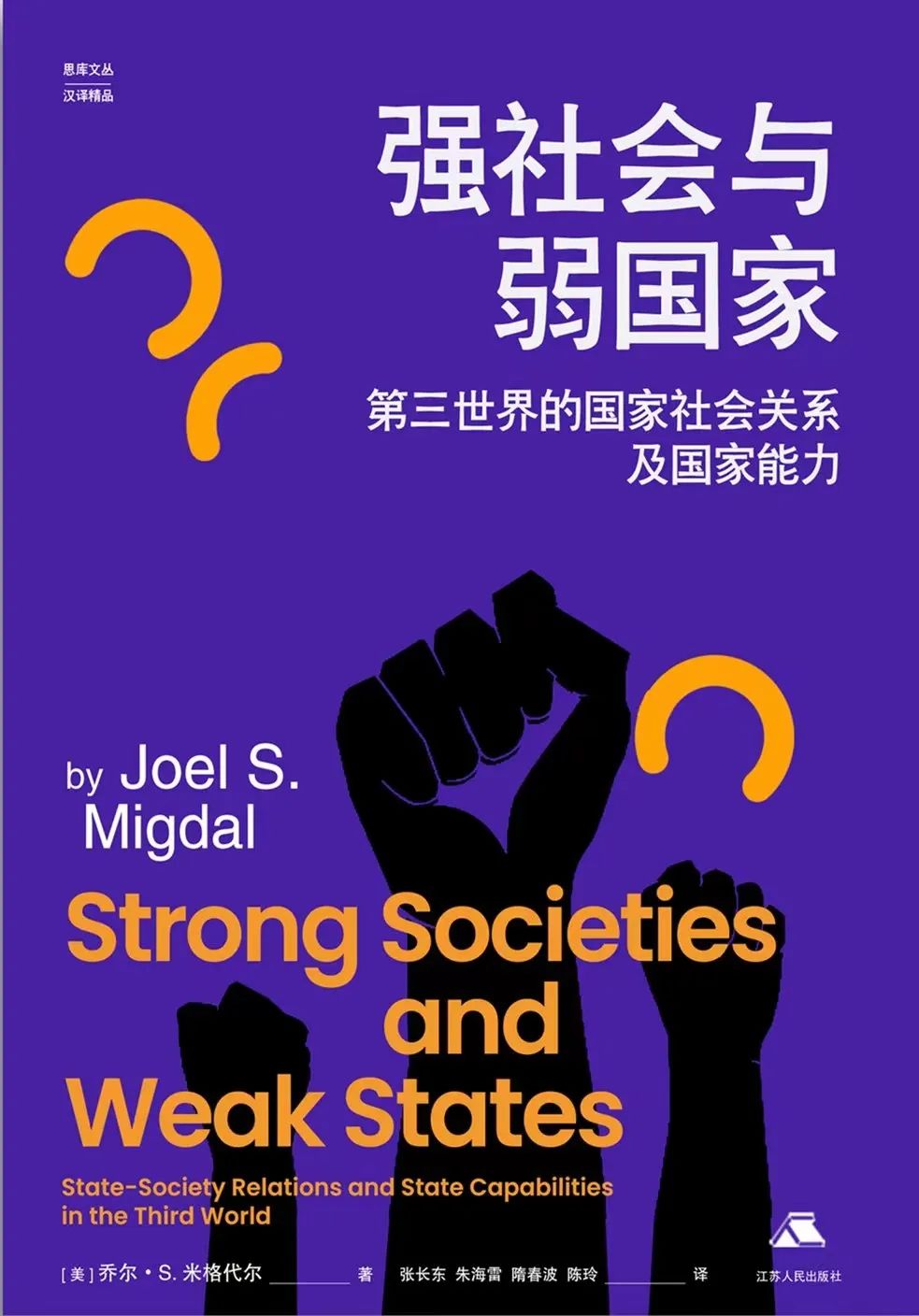
喬爾·S.米格代爾(Joel S. Migdal)著《強社會與弱國家:第三世界的國家社會關系及國家能力》封面
這一結論讓我想起了政治學對於民主誕生決定因素的研究。民主製度的興起與經濟發展一樣,是一個廣受社會科學研究者關註的重要議題☎。在過去一個世紀的時間裏,學術界曾嘗試用收入、不平等、資源依賴等多種結構性變量🦹♀️,為民主製度的產生做系統性解釋👮♂️。然而最近二十年日益形成的一個共識是,民主製度在一個國家的立足,與其說是某些系統性力量的驅動,不如說是偶然性事件的結果。同理🎢,在回答政府為何能有效促進發展這一問題的時候,這種對“偶然性”的尊重可能同樣是必要的。就像蘭小歡在書的結尾處所說:“(要理解發展過程)必須理解初始條件和路徑依賴🙋🏽,對‘歷史’的延續性和強大力量心存敬畏,對簡單套用外來理論心存疑慮🚻。”
(《置身事內:中國政府與經濟發展》,蘭小歡著,上海人民出版社二○二一年版)
* 文中圖片未註明來源者均由作者提供
(本文原載於《讀書》2024年5期新刊)
轉載本網文章請註明出處